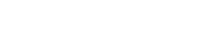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 。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 。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 。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 。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 。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 。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 。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 。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 。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采访人员,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 。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 。《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
五十年过去了 。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拆得七七八八 。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颜色依旧鲜艳 。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 。“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子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 。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 。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渡假村” 。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 。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 。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 。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 。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 。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 。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 。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 。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 。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 。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万 。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推荐阅读
- 如何给叛逆期的孩子沟通 叛逆期的孩子该怎么沟通
- 卢沟桥属于哪个省 关于卢沟桥属于哪个省
- 柳州融水双龙沟森林公园暑期活动一览
- 柳州融水双龙沟森林公园自驾怎么去 柳州融水双龙沟森林公园自驾怎么去机场
- 柳州融水双龙沟森林公园门票价格+地址
- 融安双龙沟和石门仙湖 2022融安石门仙湖景区自驾游攻略
- 柳州双龙沟景区门票价格一览表 柳州双龙沟景区门票价格一览
- 柳州双龙沟景区电话+地址+开放时间信息一览
- 门票+交通指南 2022柳州融水双龙沟景区游玩攻略
- 柳州市双龙沟景区 2022柳州融水双龙沟景区开放时间